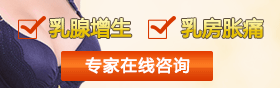发布时间:2016-04-18 点击阅读:
脑缺血的细胞死亡:坏死或凋亡?
中华神经科杂志 1998年第5期第31卷 学术争鸣
作者:叶诸榕
单位:200032 上海医科大学病理学教研室
【编者的话】 目前,脑细胞凋亡的研究报道很多,但对“凋亡”本质的认识尚不清楚。本文作者概述了“凋亡”与“坏死”的各方面异同,值得读者认识、参考和进一步讨论。
近年来,关于细胞死亡机制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兴趣,细胞坏死和凋亡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细胞死亡机制。由于多种细胞外因素,如供能的衰竭、离子交换的异常、过氧化物及自由基的生成等因素,造成浆膜的破坏,导致细胞死亡,称为坏死。坏死为病理性细胞死亡。而细胞凋亡归结为一系列基因(死亡基因)的表达,引起核酸内切酶和蛋白裂解酶的合成,导致dna的断裂,并出现一系列形态改变。因此,有人比喻细胞坏死为“他杀”,而细胞凋亡为“自杀”。凋亡可出现在胚胎发育阶段,可为生理性细胞死亡,如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神经元的死亡。也可出现于肿瘤细胞。这些细胞当时都处于活跃的分裂状态中。然而,farber[1]指出,“对细胞凋亡的兴趣导致了有关文献量的急剧增加,以致细胞凋亡成了细胞生物学和细胞病理学中最为混乱和难于理解的领域。”“细胞凋亡被某些学者,尤其是非病理学工作者认为是与坏死完全不同的细胞坏死类型”。farber[1]认为“细胞坏死涉及到一系列生物化学改变,目前,仍不清楚何处是生和死的转折点(point of no turn)。对于细胞死亡的判定,实际上仍是依据细胞死亡后的一系列改变。因此,目前提出不同的细胞死亡类型是不合适的。”
近年来,不少文献引证kerr 60年代的论文,认为是kerr发现并命名了细胞凋亡。事实上,1885年flemming观察到退行性的卵泡上皮细胞的染色质浓聚,呈现目前被认为是细胞凋亡典型形态的半月状或固缩成小体状的染色质;1886年nissen在哺乳期乳腺中也观察到类似的改变[2]。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些描述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近来,由于发现在发育生物学中所谓细胞程序死亡(programmed cell death)需要rna和蛋白质的合成,又重新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3]。
细胞凋亡的识别,可有形态依据和生化依据,然而,到目前为止,形态改变仍是最佳的识别依据[3]。目前公认的细胞凋亡的识别依据是:(1)发生于散在单个细胞;(2)细胞的染色质可形成一个大的新月体样帽状改变,核膜逐渐曲折,包裹浓聚的染色体块,并分散于胞浆之中;(3)胞浆显示内质网扩大,结构完好的线粒体和其他细胞器紧靠排列,胞质浓缩。细胞膜局部突起(出芽),内含致密染色质小体或部分细胞器。最终,这些突起和细胞分离,形成凋亡小体;(4)凋亡细胞的碎片被巨噬细胞或邻近细胞吞噬消除。凋亡细胞不吸引中性粒细胞[2,4]。
坏死则常累及许多相邻的,甚至于一大片细胞,其核可出现核浓缩,核碎裂及核溶解等改变。由于核的溶解可形成鬼影细胞,胞浆呈现深伊红色改变。坏死的细胞可吸引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5]。电镜下坏死细胞染色质可呈块状,边置,核膜可呈不规则状,因此,在某些切面上可出现类似细胞凋亡的图像,然而其细胞器可肿胀,核膜可出现破裂。神经元坏死则形成红色神经元,对其形态改变已有详尽描述[6]。
wyllie等[4]报道凋亡细胞的dna裂解成180~200 bp的片断,其凝胶电泳可出现梯状条带,并认为梯状条带是识别细胞凋亡的主要生化依据。因为坏死细胞dna凝胶电泳呈现连续的涂抹状,并不出现梯状条带。由于早年不少实验是观察体外细胞培养的结果,并不完全适用于体内实验。原位dna片断专门标记法(tunel)[7]及原位dna末端标记法(isel)[8]先后问世,以期在原位检测dna片断。加之市售药盒的出现,随后的大量文献以此技术观察细胞凋亡的出现(包括脑缺血),却造成了混乱。下列原因造成细胞死亡研究领域中的混乱。
1.细胞凋亡的生化判别依据的不可靠:由于dna裂解成180~200 bp片断而出现的梯状电泳和细胞凋亡的形态并不一致。它可以裂解为300 bp~50 kbp的片断,或可不出现梯状电泳。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坏死的早期同样可出现dna梯状电泳,这就是说梯状电泳并非细胞凋亡的特异性判别标准[9]。
有报道,tunel不能区别细胞凋亡、坏死和自溶性细胞死亡[10,11]。对于isel也有类同的报道[12,13]。tunel和isel的原理都是测定dna的3′-oh末端[7,8]。在细胞凋亡、坏死和自溶性死亡中,只要有dna裂解,其3′-oh末端数量都会有所增加,因此,上述两法不可能作为原位测定有无细胞凋亡的可靠方法。而市售tunel药盒的假阳性率特别高,甚至可导致细胞核和胞浆的同时染色[13]。遗憾的是,当前大量文献报道都是以tunel的阳性染色判别脑缺血是否有细胞凋亡的存在。而且这类文献还经常被引用。
dna裂解和细胞是否存活并不一致,细胞损伤伴dna裂解出现于细胞死亡以前,此时尚可伴有dna的修复,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可修复成功[14]。
2.对细胞凋亡形态改变的不确切的描述,对不具有良好形态训练的研究者产生误导作用。wyllie等[4]以及majno等[2]在他们各自的综述中将核固缩和核碎裂描写为仅在细胞凋亡中出现的现象。wyllie等在他们的综述中描述坏死时仅用了寥寥数字:整个细胞成为鬼影细胞;而谈到细胞凋亡时则详细描述了核固缩和核碎裂的现象。作者没有交代鬼影细胞形成过程中细胞核的衍变。majno等在整段关于细胞凋亡的描述中写到:核碎裂,以往仅仅作为一种单纯的形态描述,在其被认为是细胞凋亡的一种特征以后,则赋予其新的意义。进而作者又提到:作为缺血的结果,神经元显示核碎裂者可出现细胞凋亡。然而,majno等引用的文献恰恰是缺血引起神经元坏死而不是细胞凋亡[15]。这样的综述给读者一种印象,即核固缩和核碎裂仅仅出现于细胞凋亡,这种观点是违背病理学基本原则的,核固缩和核碎裂正是细胞坏死时的基本改变[5],也是被长期病理实践所证实的。因为将核碎裂和核固缩归结为细胞凋亡,majno等对于细胞死亡的描述必定不能概括所有病理学中细胞死亡的改变,于是提出了细胞肿胀死亡的概念,以将不能归结为细胞凋亡的细胞死亡囊括进去,并作为和细胞凋亡相对应的一种坏死机制。根据肿胀死亡的理论,缺血可导致细胞及细胞器肿胀,最后导致细胞膜破裂,细胞坏死。这种假设提出后,受到冷遇,因为它不符合实际情况。神经元缺血坏死时演化成红色神经元,胞体固缩,胞浆呈深伊红色,胞体固缩,继而可出现核固缩、核碎裂或核溶解,最终形成鬼影细胞。鬼影细胞可逐渐湮灭,也可被激活的小胶质细胞和(或)巨噬细胞所吞噬。此外,为了强调核固缩和核碎裂与细胞凋亡的关系,wyllie等[4]以及majno等[2]都没有描述病理学实践中常见的凝固性坏死。因缺血引起的肾脏、脾脏、肝脏的凝固性坏死,以及脑缺血所致的脑梗死,都出现成片的细胞死亡,吸引中性粒细胞,这些都不符合细胞凋亡的改变。然而,就在这些病理改变中核固缩和核碎裂却是常见的改变。因此,必须指出,核固缩和核碎裂并非仅仅出现在细胞凋亡中,记载它们出现在细胞坏死中的历史可能更为长久。
核固缩不仅仅意味着染色质浓缩,而且还意味着核膜的皱缩。由于核膜皱缩,某些切面的电镜照片可出现核内假包涵体(核膜内陷),或染色质外突,可与细胞凋亡的描述极为相似,有报道以此认为是细胞凋亡,此时应注意胞浆的改变,因为在细胞凋亡和坏死中的胞浆改变是不一致的。此外,还必须认识到,脑缺血时胞浆中出现高电子密度颗粒,可以是内化的浆膜的蛋白聚结而不是细胞凋亡的证据[16]。
3.对神经系统细胞组分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神经系统不仅表现为其结构和功能的精巧和复杂,其细胞组分也十分复杂。在中枢神经系统中,胶质细胞的数量是神经元的10倍,其中50%是星形胶质细胞。星形胶质细胞的总体积在人类额叶可占20%~50%[16]。鉴于胶质细胞的数量以及其在中枢神经系统损伤中所占有的体积,在各种原因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损伤中,胶质细胞也常受累,例如星形胶质细胞的肿胀往往是最早出现的形态改变。因此,用特异的细胞标记区分出现细胞凋亡变化的细胞类型就显得十分必要。遗憾的是,有关脑缺血中出现的细胞凋亡的报道,大多没有进行细胞分类。更有甚者,照片上报道tunel阳性荧光,而文字说明在胼胝体内神经元出现凋亡。胼胝体中没有神经元,仅有少突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因此,呈tunel阳性荧光着色者应是胶质细胞。更值得注意的是浸润于脑缺血区的中性粒细胞,当其在原位死亡后,其多形分叶核可出现类似某些凋亡细胞的形态特征。因此,区别细胞类型是绝对必须的,而市售的荧光标记凋亡药盒(apopkit,tunel kit)不利于细胞类型的区分。
细胞凋亡之所以具有吸引力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发生脑缺血的时间和出现神经元死亡间有一个时间间隔,其最典型的例子是所谓延迟的神经元死亡(delayed neuronal death, dnd)。10分钟的脑缺血可导致迟到28天仍出现神经元坏死[17],其病理改变不但形态不符合细胞凋亡的改变,其意义和时相都不符合细胞凋亡的概念。到目前为止,尽管有不少的文献报道,但仍不能提供绝对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脑缺血时存在细胞凋亡。由于对于脑缺血是否真正存在细胞凋亡尚不能确定,报道某些制剂对防止(或保护)脑缺血时细胞凋亡则更不能令人信服。这些制剂可作用于某一生物化学环节,阻止细胞死亡的发生,但可能并不一定是细胞凋亡,因为在脑缺血动物实验中是否有细胞凋亡尚不能确定。
对于细胞凋亡研究最大的功绩是对细胞死亡过程中的基因控制和相应的生物化学改变有了全新的了解,但是如果将这些基因改变和细胞凋亡联系起来的是目前认为不再可靠的生化识别标准,那么,其结论也应作重新评价。此外,这些基因并非作为完全独立的内因起作用,而可在外因的诱导下起作用,例如辐射、抗肿瘤药物、轻度过热、激素或生长因子的撤除、抗apo-1抗体或抗fas抗体、细胞毒性淋巴细胞[18]及氧化剂(如过氧化氢,脂质过氧化酶及细胞内的自由基)。最近,线粒体在细胞凋亡发生中的作用受到了重视,认为线粒体在细胞凋亡的共同通路中起作用[19],外源性氧化物可影响线粒体的电子传递以及由磷脂酶a2激活的花生四烯酸的代谢。很多细胞凋亡是继发于线粒体通透性的改变。氧化剂如过氧化氢、自由基、线粒体、电子传递与细胞呼吸及花生四烯酸等,都是人们熟知和细胞坏死有密切关系的物质,现报道和细胞凋亡有关,而这些细胞凋亡和细胞坏死一样,可由外源性因子、胞浆性因素所引起。细胞坏死的概念之一就是胞浆性细胞死亡。因此,科学的进展使细胞凋亡和细胞坏死的绝对界线变得模糊起来。二者可能是细胞死亡的不同侧面而不是绝对分割的二种机制。生与死是生命的二个对立而又相互关联的现象,对生和死的研究是生命科学的二大互相联系而又独立的领域,它们都和生命的本质相关联。因此,不可能指望用相对简单的某一种或几种方法来阐明其本质。期待日后有更精确可靠的方法和技术来探索这些现象。
参考文献
1 farber e. programmed cell death: necrosis versus apoptosis. mod pathol, 1994,7:605-609.
2 majno g,joris i. apoptosis, oncosis, and necrosis. an overview of cell death[see comments]. am j pathol 1995, 146:3-15.
3 hockengery d. defining apoptosis[comment][see comments]. am j pathol, 1995, 146:16-19.
4 wyllie ah, kerr jf, currie ar. cell death: the significance of apoptosis. int rev cytol,1980, 68:251-306.
5 mitchell rn, cotran rs. cell injury, death, and adaptation. in: kumar v, cotran rs, robbinssl, eds. basic pathology. 6th ed. london: wb saunders company, 1997.11-15.
6 garcia jh,liu kf, ho kl. neuronal necrosis after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in wistar rats progresses at different time intervals in the caudoputamen and the cortex. stroke,1995,26:636-643.
7 gavrieli y,sherman y, ben-sasson sa. identification of programmed cell death in situ via specific labeling of nuclear dna fragmentation. j cell biol, 1992,119:493-501.
8 wijsman jh, jonker rr, keijzer r, et al. a new method to detect apoptosis in paraffin sections: in situ end-labeling of fragmented dna. j histochem cytochem, 1993,41:7-12.
9 dong z, saikumar p, weinberg jm, et al. internucleosomal dna cleavage triggered by plasma membrane damage during necrotic cell death. involvement of seine but not cysteine proteases. am j path, 1997,151:1205-1213.
10 grasl-kraupp b, ruttkay-nedecky b, koudelka h, et al. in situ detection of fragmented dna (tunel assay) fails to discriminate among apoptosis, necrosis and autolytic cell death: a cautionary note. hepatology, 1995,21:1465-1468.
11 yasuda m,umemura s,osamura ry, et al. apoptotic cells in the human endometrium and placental villi: pitfalls in applying the tunel method. arch histol cytol, 1995, 58:185-190.
12 schmidt-kastner r, flissv h, hakim am. subtle neuronal death in striatum after short forebrain ischmia in rats detected by in situ end-labelling for dna damage. stroke, 1997,28:163-170.
13 petito ck, roberts b. evidence of apoptotic cell death in hiv encephalitis [see comments]. am j pathol, 1995, 146:1121-1130.
14 masters jn, finch ce, sapolsky rm. glucocorticoid endangerment of hippocampal neuron does not involve deoxyribonucleic acid cleavage endocrinology, 1989, 124; 3083- 3088.
15 ahdab-barmada m, moossy j, nemoto em, et al. hyperoxia produce neuronal necrosis in the rat. j. neuropathol exp neurol, 1986,45:233-246.
16 hansson e.astroglia from defined brain regions as studied with primary culture. prog. neurobiol, 1988,30:369-397.
17 du c, hu r, csernansky ca, et al.very delayed infarction after mild focal cerebral ischemia: a role for apoptosis? j cereb blood flow metab,1996,16:195-201.
18 kerr jf, winterford cm, harmon bv. apoptosis: its significance in cancer and cancer therapy. cancer, 1994,73:2013-2026.
19 schapira ah. mitochondrial disorders. curr opin neurol, 1997,10:43-47.
(收稿:1998-02-24 修回:1998-07-14)
温馨提示:重在预防,加强锻炼、增强体质、生活饮食规律、改善营养。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有助于提高抵抗力,是预防疾病最好的办法。